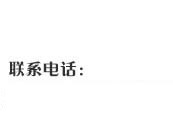貴州貴陽討債說*罪
作者:律師咨詢發布時間:2019-04-13 13:56
1��、案情 公訴機關:上海市某區*��。 被告人:范某某。 上海市某區經審理查明:2007年12月���,劉某向上海市交通銀行申領洋雙幣信譽卡一張。2008年2月,被告人范某某向劉某借用該信譽卡����,在明知沒有還款才能的狀況下�,持該信譽卡經過消費�、提現等方式累計本金錢2萬余元。期間,交通銀行屢次經過電話�、制發通知書等方式停止催討���,被告人范某某超越3個月仍不出借����。2012年3月25日���,被告人范某某主動至某某投案���,照實交代上述事實����,并退賠涉案全部贓款�����。 2����、審訊結果 上海市某區以為����,被告人范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持有的信譽卡超越規則期限��,并且經發卡銀行屢次催收���,超越規則的期限仍不予出借�,數額較大,其行為曾經構成信譽卡罪�����,應依法予以懲辦�����。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范某某的立功事實分明�����,證據的確充沛,定性正確�����。被告人范某某主動至某某投案�,主動交代立功事實,系自首����,且退繳了全部贓款�����,補償了被害單位的經濟損失,確有認罪悔罪表現���,可依法和酌情從輕處分,并可適用緩刑����。據此�,為維護公私財富一切權不受進犯�����,維護國度法制����,按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四)項��、第二款����,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條之規則,判決: 一����、被告人范某某犯信譽卡罪���,判處6個月�,緩刑1年�����,并處分金錢2萬元���; 二�����、被告人范某某退繳的贓款錢2萬元,發還被害單位交通銀行。 一審宣判以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亦未抗訴�,判決已發作法律效能��。 3����、評析 被告人范某某如持有本人申領的信譽卡超越規則期限���,并且經發卡銀行屢次催收仍不予出借���,當屬刑法意義上歹意型信譽卡行為����。而在本案中,被告人范某某用于歹意的信譽卡系借用別人。對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歹意型信譽卡罪的主體能否僅限于合法持卡人(以下簡稱持卡人),能否包括實踐運用人(以下簡稱運用人)?歹意的行為人與持卡人不同一的情形下����,誰應當承當相應的刑事義務�?對此�,存在以下幾種觀念: 第一種觀念以為,劉某與范某某都應當構成立功。劉某違背規則將信譽卡借與范某某運用�,而范某某施行了歹意的行為�,二者應當共同承當相應的刑事義務�。 第二種觀念以為,劉某構成歹意型信譽卡罪,范某某不構成立功���。由于本罪的主體是合法持卡人,劉某作為合法持卡人,明知不得將信譽卡借與別人運用�,依然有償出借給范某某��,應當承當相應的風險和結果。范某某不具備適格的主體身份。 第三種觀念以為,在掃除共同立功的前提下���,劉某不構成立功,范某某構成歹意型信譽卡罪。依據刑法行為與義務同在的準繩��,歹意的刑事義務應當由行為人范某某承當�����。劉某既沒有共同立功的成心,也沒有施行立功行為����,不構成立功���。 筆者以為�,歹意型信譽卡罪的主體不應當僅限于持卡人�,還能夠包括運用人。詳細分以下兩種情形認定: 一��、持卡人與運用人具有共同立功成心和立功行為的���,以歹意型信譽卡罪的共犯論處��。 依據共同立功的理論����,假如有證據證明持卡人客觀上也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默許運用人的歹意行為���,契合歹意的成立要件����,則應當追查運用人和持卡人共同立功的刑事義務,認定為歹意型信譽卡罪的共犯�。 二���、持卡人無共同立功成心的���,應當對運用人以歹意型信譽卡罪論處����。 在持卡人缺乏共同立功成心��,或者無法查明持卡人具有共同立功成心的情形下,由于持卡人既無立功成心�,又無立功行為�����,不能構成立功,只能對運用人以信譽卡罪論處�。本案即屬于該情形���,應當對歹意的行為人范某某以歹意型信譽卡罪論處����,合法持卡人劉某不構成立功。理由如下: (一)依據無行為即無立功準繩�,劉某不構成立功����。 沒有行為就沒有立功�����,行為是立功的根底�。{1}刑事與民事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刑事關注的是行為人的行為形成的社會危害性����,而民事則偏重于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刑事義務強調的是本質性判別���,對刑事義務承當者的判別不能單純地以行為人在民事法律關系中的位置為獨一規范�,更不能簡單地將各主體在民事法律關系中的位置移植于刑事法律關系中。歹意型信譽卡罪中�,假如持卡人同意受權運用人運用信譽卡�,呈現歹意的情形時就觸及刑民穿插的問題����。依據民法原理,這種情形存在著兩個民事法律關系,即持卡人與銀行之間的借貸關系、運用人與持卡人之間的借貸關系�。假如運用人歹意信譽卡���,則持卡人應當向銀行承當款項的全部義務���,運用人充其量作為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持卡人固然在承當義務后能夠向運用人追償����,但這不能成為免除其個人義務的抗辯理由。但是,假如要追查刑事義務,則不能依照民事義務的認定邏輯來將持卡人作為刑事義務的對象�。由于假如持卡人客觀上不具有歹意直接的成心����,客觀上亦未施行非法占有銀行資金的行為�����,僅以持卡人的民事不法行為而追查其刑事義務�,顯然違背了本質正義理念���,違犯了無行為就無立功的準繩��。本案中的持卡人劉某客觀上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沒有施行歹意的行為��,不應當構成立功��。 (二)運用人成為歹意立功主體的合法性剖析�。 第一�����,將持卡人了解為既包括合法持卡人���,也包括其他實踐用卡人���,并未打破持卡人的合理內涵�。有觀念以為�����,《信譽卡業務管理方法》(以下簡稱《方法》)第三十六條規則:“信譽卡僅限于合法持卡人自己運用�,持卡人不得出租或轉借信譽卡及其賬戶”���,因而刑法中的持卡人也只能限于合法持卡人。筆者以為,據此解讀刑法意義上的持卡人根據并不充沛�。同樣的詞語在不同部門法中的外延會有較大的不同���,同樣���,刑法對同一用語的解釋不一定就完整照搬前置法的規則����,比方刑法對信譽卡的界定就與《方法》的規則不同�。2004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經過的“關于《中華共和國刑法》有關信譽卡規則的解釋”指出:“刑法規則的信譽卡,是指由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具有消費支付、信譽����、轉賬結算、存取現金等全部功用或者局部功用的電子支付卡�����。”《方法》第三條規則:“本方法所稱信譽卡�,是指中華共和國境內各商業銀行(含外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以下簡稱商業銀行)向個人和單位發行的信譽支付工具����。信譽卡具有轉賬結算����、存取現金、消費信譽等功用�。”可見���,刑法規則的信譽卡范疇大于《方法》的規則�。因而�����,筆者以為���,歹意型信譽卡罪的主體不應當僅限于《方法》規則的合法持卡人�����。 第二,立功的實質是對立功客體的進犯���。刑法的目的在于維護客體����,個罪在司法理論中的解釋應當以客體維護為目的。信譽卡罪規則在我國刑法金融立功中,其進犯的主要客體是國度金融管理次序��。歹意型信譽卡立功打擊的是那些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實踐采用歹意信譽卡的方式施行了非法占有銀行資金、毀壞金融次序的行為。在此意義上�����,無論能否屬于合法持卡人�,只需行為人的歹意行為毀壞了金融管理次序和制度,就對信譽卡罪維護的法益形成了損傷�����,就應當追查行為人的刑事義務����。 第三,后一行為的刑事違法性并不因先行行為無效而被掃除��。有觀念以為��,持卡人違背規則將信譽卡借與別人的行為屬于民事法律上的無效受權����,假如發作了歹意的結果,應當由持卡人承當相應的法律結果�����。筆者以為�,前行為能否合法有效并不影響刑法對后行為的評價。如固然經過偽造國度機關公文�����、擔任國度工作人員職務的行為自身屬于無效的法律行為���,但其應用該國度工作人員身份施行職務立功行為的�����,應當以偽造國度機關公文、罪和相應的職務立功追查刑事義務����,實行數罪并罰����。固然持卡人將本人的信譽卡借與別人違背了《方法》的規則���,但不能將民事法律關系中義務認定的邏輯適用于刑法���,并以此掃除刑法違法性����,應當依據運用人的行為追查其相應的刑事義務。因而,固然持卡人劉某違背規則將信譽卡借與范某某運用�����,但并不影響對范某某歹意行為刑事違法性的評價���。